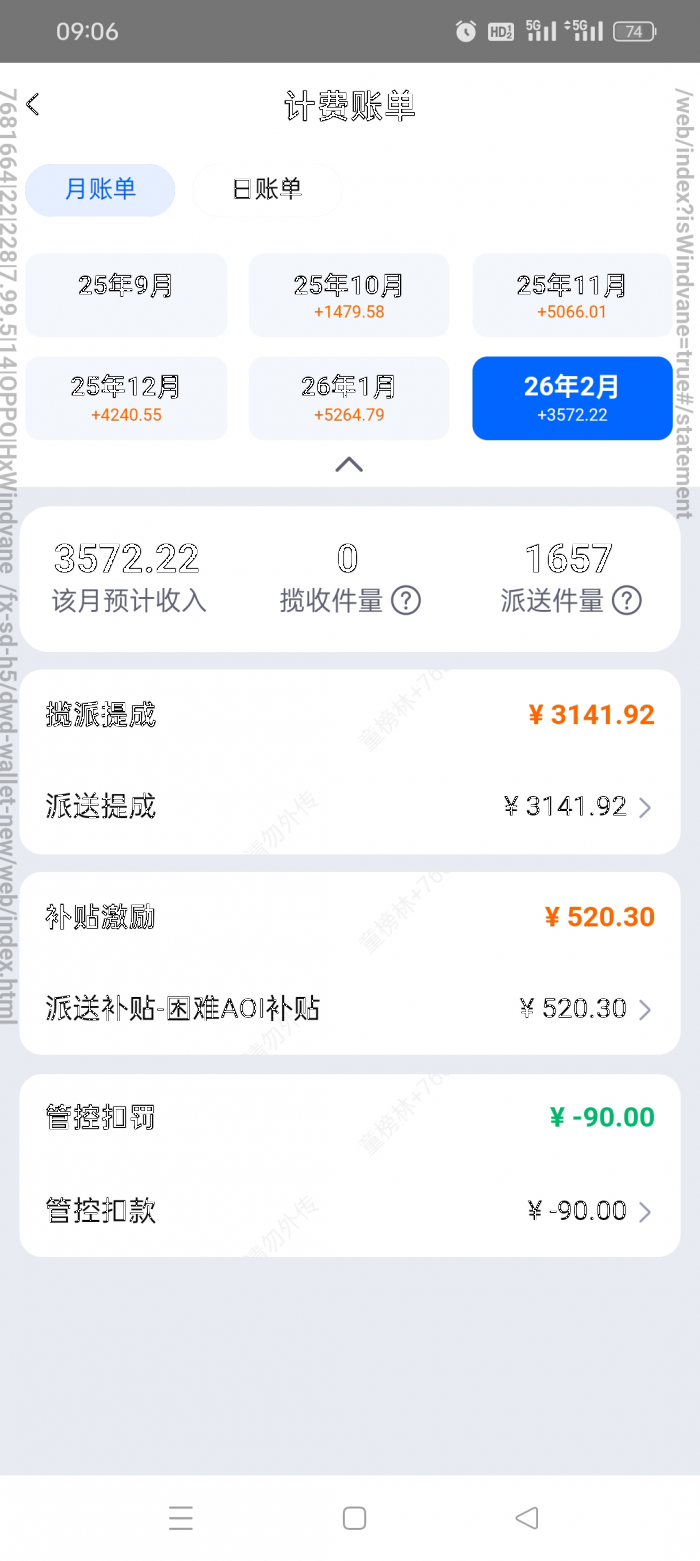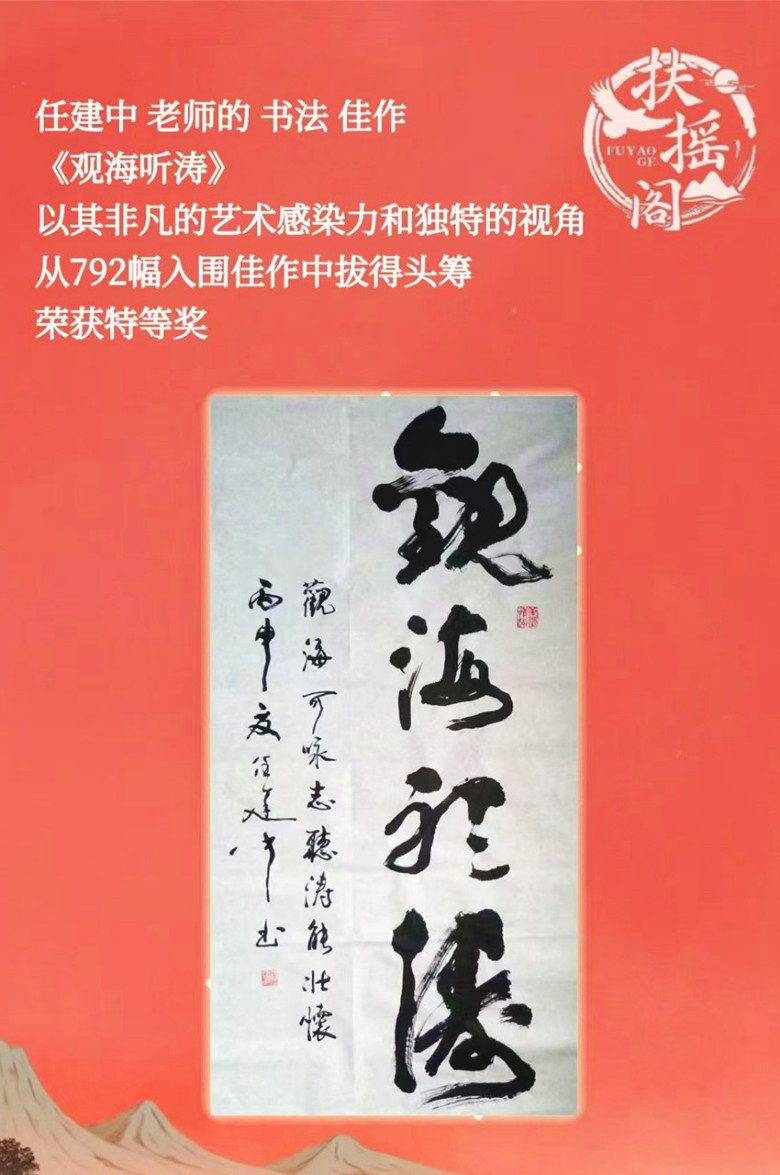《青春之歌》的阅读回忆
在读初中时,虽然上学时不需要去参加生产队的劳动,但在星期天和放忙假的时候,父母亲总要让我去队里挣工分。到了读初二时,更是如此。当时的父母们都把挣工分看得很重,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年底的分配——谁家不想在年终分红时多分到几元钱呢?
就在1971年春耕时节,有一次我和生产队的妇女们一起在麦田里除草。劳动间隙小憩时,我的一位堂嫂坐在田埂上,给几个年轻姑娘讲故事。这位堂嫂比我大十多岁,听说念过初中,人也生得小巧玲珑,一双大眼睛忽闪忽闪的,显得格外聪慧。我也凑过去坐在她们旁边,想听听这位堂嫂又在讲什么新鲜故事。
因为我刚赶过去,没听到开头,只听她继续说道:
“反抗包办婚姻出逃的林道静,有一天在北京的北戴河投海自尽,刚巧被北京大学的学生余永泽救起。余永泽浪漫的谈吐和君子般的风度,让绝望中的林道静产生了爱情的幻觉。两人你来我往,愈谈愈投缘,真有几分相见恨晚的感觉。两个年轻人耳鬓厮磨,就像干柴碰上了烈火,爱情的火焰熊熊燃烧起来,于是很快同居了。在品尝到爱情的甘甜之后,又火速结了婚。
但是婚后,林道静不甘心做家庭主妇。她觉得自己天天围着锅碗瓢盆转,日子过得既无聊又无味,她渴望投身社会,心里装着自己的理想。后来她因宣传抗日被迫离校,在遭遇一连串波折后,渐渐发现丈夫余永泽完全变了一个人,和当初恋爱时的模样判若两人。他为人势利刻薄,只追求个人名利,根本不顾国家与大众的利益。夫妻之间的精神隔阂,一天天加深。
后来林道静结识了共产党学生领袖卢嘉川,开始接触革命思想,并积极参与活动。余永泽知道后,强烈反对她参加学生运动,认为应该‘多研究些问题,少谈些主义’。两人在政治立场和人生理想上,产生了根本的对立。
有一天,卢嘉川遭敌人追捕,躲到林道静家里。但余永泽为了私利,不顾林道静的再三请求,狠心将卢嘉川赶出家门,最后导致卢嘉川被捕遇害。这件事让林道静彻底看清了余永泽的自私与反动本质,她愤而与余永泽决裂,离家出走,投身革命。”
讲到这里,堂嫂清了清嗓子说:“今天就讲到这里,马上又要干活了!”围坐听故事的人都“意犹未尽”,有的催促她再讲一会儿,有的追问后来林道静怎么样了。我也急不可耐地问:“嫂子,你讲的故事叫什么名字?是哪本书上的?”堂嫂见我这个愣头青也关心起林道静来了,便笑着说:“你这个小叔子,不是个小秀才吗?怎么连《青春之歌》这本书也不知道?这本书可好看啦,可惜现在看不到,也不允许看,因为它属于‘毒草’!”
堂嫂的话一点没错。当时正值“文化大革命”,几乎是又一场“焚书坑儒”。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,所有长短篇小说,不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,只要里面涉及爱情、人情的内容,一律被判定为“毒草”,谁也不能传阅。一时间,爱读书的人几乎无书可读。可想一想,哪一本书不写人和事?哪一本书不写男和女?人本就有七情六欲,怎么可能离得开一个“情”字?但堂嫂口中的《青春之歌》,却让我梦寐以求,对林道静更是“牵肠挂肚”。一连好多天,我都为《青春之歌》辗转反侧,真正到了食不甘味的程度。
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,到哪里去寻找《青春之歌》呢?经过多方打探,我终于找到了一个“活水源头”——从上海、无锡、常州、溧阳城里下放到我们村插队的知青们手里,都有书。而且据我所知,有一个上海知青手里就藏着《青春之歌》这类爱情小说。找到了淘书的门路,我便开始动脑筋,想办法接近他们。我当时比知青们小三四岁,或者七八岁,尤其是在老三届眼里,我不过是个“小不点”。那么,我该怎么去和他们“交朋友”呢?
我从小就是个“鬼头王”,脑子活络。当时我想,这些从大城市来的知青,过不惯农村的清苦生活,想吃鱼吃肉,经济上又不允许,但谁不想偶尔沾点荤腥?于是我想出了一个妙招:利用我是个捕虾捉鱼捞贝壳的小能手,经常给他们送些小鱼小虾小贝,帮他们解解馋,用这个来联络感情。
说干就干!一天放学后,我提着渔网,背着鱼篓下了湖。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奋战,我捕到了三四斤鱼虾。一回到家,我就把鱼虾分开洗净,趁着同住一屋的上海和常州知青刚下晚工,回到“知青宿舍”的时候,我敲门说:“知青大哥,我送点鱼虾给你们吃,是我自己捕的,不要钱!”说完,我把装着鱼虾的小竹篮往他们宿舍里一放,扭头就跑。
过了一天,也是在傍晚歇工时分,我又给他们送去蛤蜊和螺蛳,顺便取回前天盛鱼虾的竹篮。正当我转身要走时,一位知青大哥一把拉住我,问我叫什么名字,为什么总送鱼虾给他们吃。我被问得脸都红了,局促地说,想借你们的小说书看看。几位知青大哥听了,都笑起来。记得其中一位说:“小老弟来者不善,李向阳进城,是有目的的啊!”但他们还是同意把书借给我看,只是必须约法三章:一是只准自己一个人看;二是不得外传;三是一看完就还。我连忙点头答应,还保证永远守住这个“秘密约定”。他们几个人分别借给我一本小说,其中就有我梦寐以求的《青春之歌》。
我如获至宝,把书揣在怀里往家跑。回到我的小窝——那时我一个人睡在一间小屋里,屋里还养着猪和羊——我先把这些书藏在床垫下,等到晚上一个人时再偷偷地看。每天吃过晚饭,我给自己那盏小煤油灯灌满油,早早躲进小窝,借着微弱的灯光,或半躺或趴在床上阅读,就像一个饥饿的人捧着香喷喷的馒头,拼命地吞食着书中的情节。夜深了,村庄静了,整个村子都沉入梦乡,我却毫无察觉,完全沉浸在小说里;公鸡打鸣了,东方泛起鱼肚白了,我仍然不知道,只是随着主人公时而欢喜,时而紧张,时而悲伤。窗户透进亮光,啊,又是一个通宵!
因为连续好几个黄昏都不去找疤头和电线杆,他们也找不到我。有一天上学路上,电线杆追着我问:“这几天吃过晚饭你跑哪儿去了?我和疤头到处找你!老地方去了好多次,你都不在!你是不是有什么秘密瞒着我们?”我故意哈哈笑起来:“有什么秘密?不过是瞒着你们偷偷‘啃馒头’罢了!”电线杆一听急了,瞪着眼叫道:“你这小子怎么变样了?有好东西吃竟然不告诉我和疤头,这还算好朋友吗?”我一边笑一边对他说:“就是不给你们吃!疤头肯定吃不了,你也许不想吃,所以我就一个人悄悄吃了!”电线杆听了,抓耳挠腮,如坠云雾之中。
有一天晚上,疤头带了几个煨红薯,想找我和电线杆一起分享。但他找到了电线杆,却找不到我。我在小窝里听到疤头和电线杆一声声叫唤,想答应,又怕他们耽误我读书,更怕他们泄露我的秘密。正在犹豫时,听到电线杆对疤头说:“这么早,他总不会已经睡了吧?我们去他家的养猪小屋看看,他是不是真睡了。不然,他能躲到哪里去‘啃馒头’呢?”我一听这话,立刻翻身起床,吹灭煤油灯,把已经闩上的门拉开,钻到了床底下。
疤头跑在前头,先“咚咚咚”敲了几下门,电线杆在后面跟着喊了几声我的名字。见没动静,他们便推开门。电线杆还到我床上摸了摸,说:“没睡,能躲到哪儿去呢?难道真有什么秘密瞒着我们?”疤头说:“别找他了,我们俩去老地方吃煨红薯,馋死他!”
等他们走了,我也觉得肚子饿了。那带着焦香味的煨红薯,怎能错过?于是我悄悄跟在他们后面,一直跟到老槐树边的草垛旁。疤头刚从破衣袋里掏出煨红薯,我突然冲上去抢了一个,大声嚷道:“你们两个人居然瞒着我吃好吃的,真不够兄弟!”两个人被我吓了一跳。电线杆回过神来才说:“是你瞒着我们吃好的!我们到处找你找不到,你倒突然从地底下冒出来了!”三个人在寂静的夜晚分享着煨红薯。红薯的香味,仿佛让夜色也变得更美了。老槐树发出沙沙的声响,小狗在村巷里轻吠,半圆的月亮在云层中缓缓流动。
吃完煨红薯,我半遮半掩地向疤头和电线杆吐露了我的秘密。疤头听了几乎没什么反应,因为小说对他来说毫无意义;电线杆听了也没太大反应,他从来也没读过一本小说,更不知道什么“林道静”。
我就是用这种方法继续淘书的。从上海知青、常州知青那里,我淘来了不少中外名著;就是用这种“夜读”的方式,我阅读了很多书。其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:《青春之歌》《红岩》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《三家巷》《暴风骤雨》《母亲》《青年近卫军》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《复活》《静静的顿河》《郭沫若剧作选》《曹禺剧作选》《周作人散文选》《鲁迅杂文选》等。林道静、郭全海、区姚、江竹筠、金环银环、季柯夫、聂赫留朵夫、扎洛莫夫……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,深深扎进了我的脑海。他们中有的让我感动,有的让我敬佩。还有郭沫若剧作《屈原》里的“雷电颂”,《孔雀胆》里阿盖公主的美丽;曹禺剧作《雷雨》中四凤的遭遇;周作人散文里扑面而来的乡土气息……都让我为之动容,为之折服。
尤其是一本本小说中的爱情故事,悄然萌动了我的“青春心房”。我对异性产生了强烈的好奇与兴趣,对身边同龄的漂亮女孩子,也萌生了朦胧的爱意。
![](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