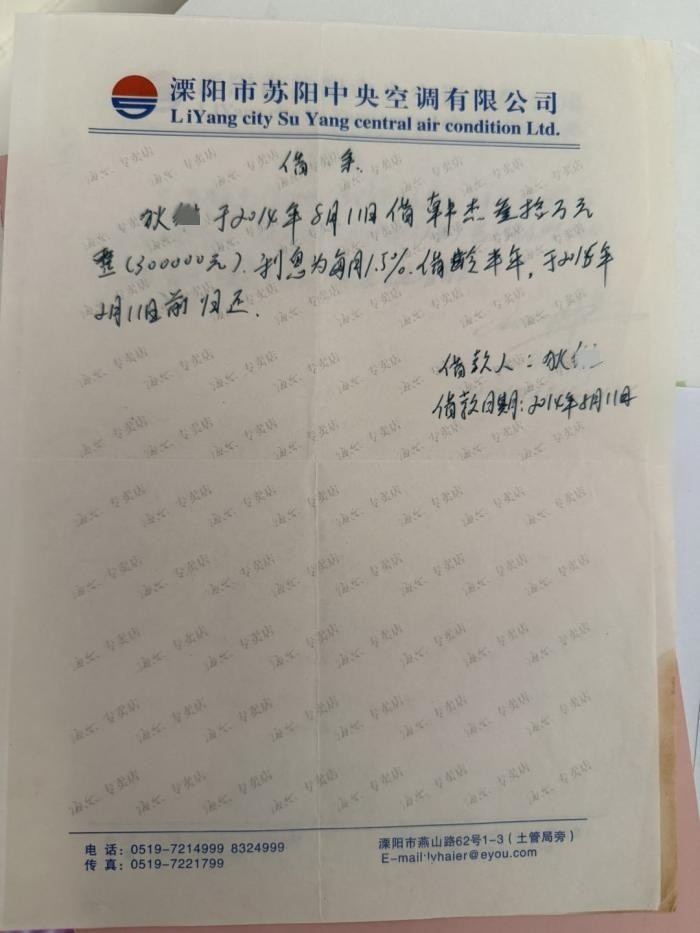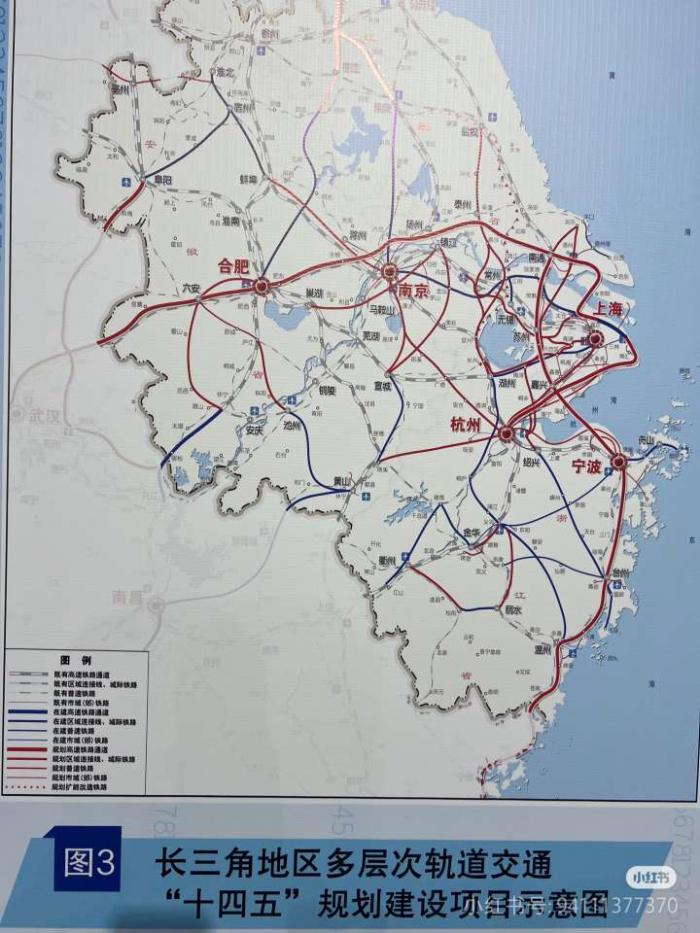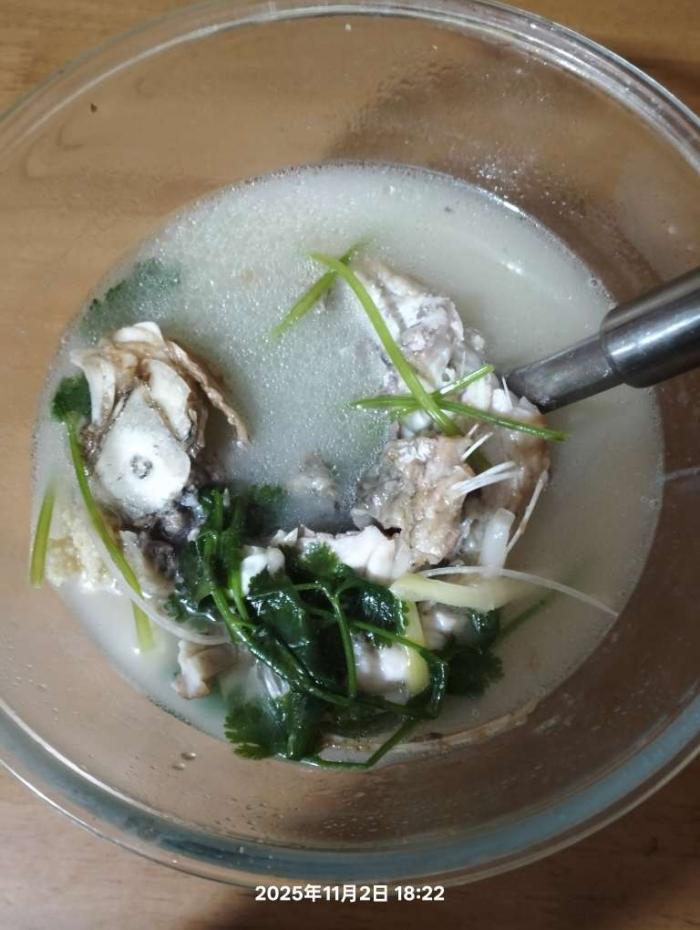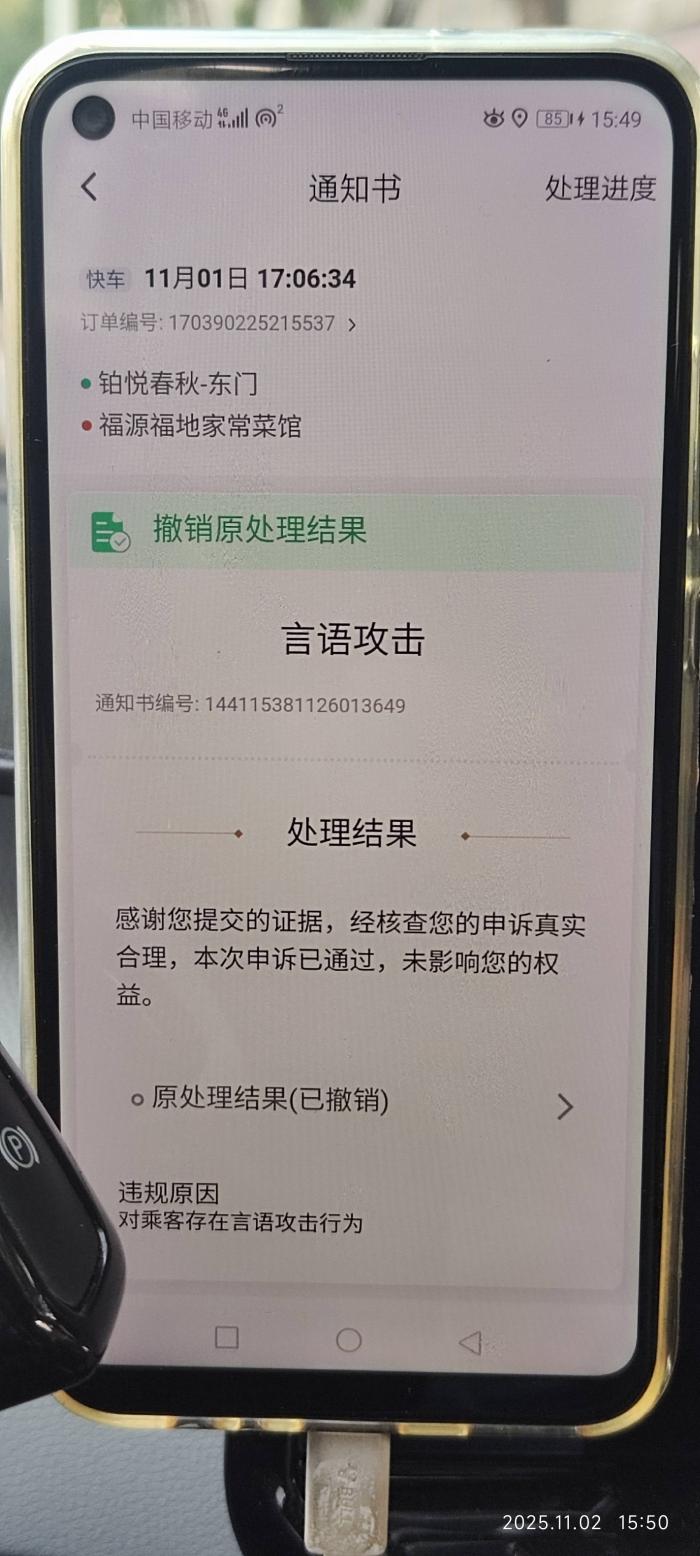2023-10-17
一川风月
来自江苏
溧阳论坛
正在消失的老事物之十四:石磨、豆腐缸、磨床、水桶挑担等——石磨圆圆出白玉
题记:许多伟人名士的所作所为,因文字的传承而千年不朽。同时,无数的平凡人却无痕无迹、无声无息,被遗弃在了历史的角落,消逝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。 在历史的筛子里,只留下伟岸和宏大。而千万小人物,活着时就一如尘埃,随风消散,默默无闻。一旦,百年、甚至数十年以后,有谁会知道他们的名和姓?有谁会认识他们所操持的器具?有谁会知晓他们所从事的工作?还有谁会体会他们的忧愁喜乐、体会他们的酸甜苦辣?又有谁会了解他们的人生、了解他们的品性呢? (三)、磨浆: “一般都是前一天晚上开始浸泡黄豆,第二天早上开始磨黄豆和做豆腐的。” 浸泡好的黄豆,一粒粒的登上石磨的“舞台”,就进入豆腐制作的重头戏——磨浆。 其实制作豆腐有很多步骤,但由干磨浆是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。因此,人们把制作豆腐就叫做“磨豆腐”。 “黄豆为什么必须磨得比较碎、比较细,才能做豆腐呢?” “黄豆磨碎、磨细了,黄豆里的蛋白质才能(提取)出来,到水里开(溶解在水中),变成豆浆。”洪芝老叔解释道,“就这样吃整个黄豆,有一部分蛋白质不能(被人)吸收,会浪费掉的。” 确实,黄豆里的蛋白质绝大部分都储存在具有细胞壁的大豆子叶细胞里面。由于,人体缺乏纤维素酶和果胶酶,无法消化细胞壁。所以,人食用整个黄豆,除了用牙齿咀嚼,破坏了植物一部分的细胞壁,释放的一部分蛋白质可被利用外,其它还有另一部分蛋白质还安静的躺在细胞壁的“怀抱”里,最后,随着粪便排出体外。 而通过石磨的研磨作用,就解决了这一难题:在磨盘的磨练下,黄豆子叶组织细胞的细胞壁被充分碾压、破坏,热好身的蛋白质(包括其它营养物质)挣脱细胞壁的束缚,获得自由,放飞自我,开启了奇幻之旅。最终,化身为一块块的“白玉”——豆腐。 但是,黄豆是不是磨的越细越好呢?这个并不是一般人想象的那样,这待后面再讨论。 “第二天,早晨2点我们就起床开始磨豆腐咧。有时候,做二桌豆腐,我半夜里12点就要起身咧。我做豆腐只是副业。白天,我还要种田的,辛苦咾。所以,一般晚上九点钟不到,我就上床睡觉咧。” “起来的第一件事,我就把泡好的黄豆倒在菜篮里,再拿到门口的河里把黄豆淘洗干净。清洗嘛,就是为啧(了)去掉漂浮的豆皮、杂质和脏物。还有,黄豆浸泡后,(气温高时,可能)会产生一股酸味,影响点浆和豆腐品质,必须把它冲洗掉。” “然后,把黄豆倒在牛头缸里,再加些清水。连水和黄豆,大概有大半缸的样范(样子)。” “第二件事就是要把石磨先清洗一遍。然后,石磨下面放一个豆腐缸(这是第一个豆腐缸)。这些事是我那位(妻子)来做的。这些准备工作做好后,接下来,才开始磨黄豆。” “磨黄豆要用到石磨。石磨有三部分组成:木制牵磨的砻臂、上下两块一套的石磨盘,还有一个木质的磨床。”![]()
因为,那时候没有机械装置,石磨完全是用人力转动的。所以,磨黄豆是一道苦体力活。 “我用的石磨原来是生产队里用的大石磨。生产队分队后,我花了150元钱把它买来的。这个石磨比一般的磨要大好些,是特大号,很重的。一般人家的石磨直径大概是40公分,我这个石磨直径有60几公分的,而且,还比人家的(石磨)厚。” ![]()
“在生产队里,正常情况,用这个磨磨黄豆的时候,要三个人配合:两个人并排站在砻臂的后面,每人双手抓住砻臂的横杠,不停的来回牵磨;另一个人就在前面拗磨,并喂豆。这样,黄豆磨起来就比较轻巧。”![]()
“到了我自家做豆腐的时候,只有我们夫妻两个人手了。磨黄豆的时候,跟《双推磨》里唱的一样,‘一人牵(磨)呀,一人拗’:我在磨后面拉动砻臂牵磨,不停地转动石磨;我那位(他妻子)要抓住砻臂最前面的‘磨横’(木支架)拗磨。同时,也要负责喂磨加料:(从牛头缸里)用小铜勺将泡好的黄豆连同水一起舀着放入石磨上方的磨眼(洞口)处。(黄豆入磨眼后,经过磨的碾压),黄豆浆就会出来咧。然后,浆流到磨床下面的豆腐缸里。” “喂磨时,加黄豆和加水的量都要控制好。水要适量,不能太多,也不能太少。” “一般的,黄豆与水的比例是1比2。一小铜勺大概舀三、四十粒黄豆,和着水共大半勺的量。” 原来,加水是为了保持石磨的润滑。但是,如果,水量加的过多,就会缩短大豆在磨片间的停留时间,以致出料快,达不到原定细度的要求。相反,水量加的过少,就会延长大豆在石磨间停留时间,以致出料慢,影响出品率。 如果,豆子放多了,研磨就会不充分,出的豆渣就相对较多。 “牵磨的速度也不能太快。太快了,磨出来豆渣的颗粒就大。”洪芝老叔又进一步向我详细介绍了磨浆时的注意要点,“牵磨的时候,磨也不能空转,磨芯里要始终有黄豆。空转时,磨发出的声音是不同的。” 总之,磨浆时,添豆和添水要均匀、适宜,磨的转速要适当和稳定。这样,才能保证磨出来的豆浆慢慢(均匀)流出、也更细腻。 可见,磨豆浆不光是一个繁重的体力活儿,里面也大有奥妙啊。 小时候,经常看大人们磨豆腐,这一点我特别记忆犹新。所以,我可以想象洪芝老叔夫妇两人磨豆腐的场景: “呀拉呀快又稳,磨儿转得像车轮”:牵磨的洪芝老叔手扶住砻臂把手,百斤重的石磨一圈又一圈地平稳旋转着。打一桌豆腐不知道要转多少圈、化多少力气,一如那沉重的生活! “哪里来的浑身劲”?生活,一切为了生活啊! 喂磨的老婶要一心两用:既要出力配合洪芝老叔拉动磨盘转动,又要喂豆。特别是喂豆时,要把握好喂的时间。因为,石磨一直不停的在转动,所以,石磨上的磨眼儿也一刻不停的在移动。要喂得准,保证一下子就得把小铜勺里的黄豆和水倒进移动的磨眼里,不能洒了。而且,每一勺的水和黄豆的量要大致均匀。倒完黄豆后,还得及时把手缩回来,准备舀下一勺。手脚慢了,就会来不及,或者被不停转动的磨上支架刮碰到。所以,喂豆的时候,喂磨人要心到、眼到、手到。 这是一项枯燥而繁重的一种机械运动:舀起,喂磨,缩回;再舀,再喂,再缩回——周而复始,反复循环。 随着石磨的匀速转动,上下两片石磨的缝隙间就会流出细腻的乳白色的黄豆糊,挂在石磨上呈波浪状的,犹如白玉一般,甚是好看。黄豆浆呈糊状堆积,当磨盘里的黄豆糊浆积到一定的量时,就会顺着磨盘处慢慢地流淌下来,哗哗地流进磨床底下的豆腐缸里。![]()
在磨浆时,两人都不说话,小屋内沉寂而有生息:牵着沉重的石磨,四周回响的是洪芝老叔呼呼的喘气声、磨钩在磨把圈里摩擦发出的咿呀声、石磨转动发出的研磨黄豆湿漉漉的钝响声、还有磨出的黄豆糊沿着下磨盘流进水桶时的汩汩声,这些声音汇聚在一起,好似一曲纯真唯美的古典弦乐四重奏。 “一般的,磨十二斤黄豆的豆浆,两个人大概需要一个小时的时间。” 用石磨人工磨豆腐,费工费时又吃力,其中人力的付出,有多累、多苦,只有做过的人才知道。 “现在,家里磨豆浆都用豆浆机或破壁机磨了,商家用上了(浆渣分离的)全自动豆腐机。机器磨,速度快、又省力。但是,用石磨做出来豆浆和豆腐(的质量)要比机器的好。”洪芝老叔深有体会的说。 “咦!这个是为什么呢?现在用机器磨黄豆,几乎没有豆渣了,磨出来的豆浆不是更细吗?”我好奇的问。 “问题就出在这里!”洪芝老叔解释道,“以前人工磨黄豆,磨出来的豆渣很粗、很多,而豆浆(相对)就少,出的豆腐率就低了;现在,机器磨黄豆豆浆量(相对)要比人工磨的豆浆要多,因此,出豆腐率比较高。”![]()
“机器磨得更细,蛋白质是更容易(溶)出来,但是,原来豆渣里的粗纤维素(被切得更细)就会(虑)到豆浆里。所以,豆腐吃起来就不十分细腻、地道咧,而且,豆腐色泽灰暗、死硬发板。” “原来如此!”我恍然大悟,笑着说。“所以,以前的豆渣,现在都变成豆腐了。以前的豆腐是黄豆里的精华做成的。难怪,两相一比,现在的豆腐相对就粗糙了,是不是这样啊?” 所以,研磨也不是越细越好,要有一定的限度。黄豆经过研磨,既要尽可能少含豆渣,使蛋白质能最大限度地溶出,又要尽可能少的把纤维素虑到浆水里。 还有,机械磨浆在加工过程中产生的瞬时高温、高压,以及经过高速研磨、切割,可能会破坏大豆的蛋白结构,破坏磷脂、维生素等营养物质,甚至还有焦糊的味道,大豆原有的香味就受到影响。 而传统的手工的方式来研磨大豆,石磨磨齿均匀运转,速度慢,不光能使黄豆充分释放蛋白质,而且,最大限度的保留了豆浆中的植物蛋白、磷脂、维生素B1、B2等营养物的结构。 “慢工出细活”。这样,石磨磨出的豆浆呈均匀一致的乳白色,无焦糊味、酸败味、豆腥味等其它异味,能最有效地保留大豆固有的浓郁清香。所以,其口感滑爽,味美异常,香甜悠长,回味无穷。而且,石磨豆浆做成的豆腐,水分少,韧度大,质地绵软柔嫩、洁白如雪、久煮不老。 “是这个理。”洪芝老叔总结说,“石磨做出来的豆浆、豆腐营养和口感更加好。” “石磨磨黄豆、柴火煮浆,还能喝上一碗热腾腾的豆浆或豆腐花。如今,怎么也吃不到过晨光那个味道了。”洪芝老叔不无遗憾的说。 确实,那些曾经熟悉的清香纯正的味道,早已消失在了那机器的蜂鸣声中了。
展开